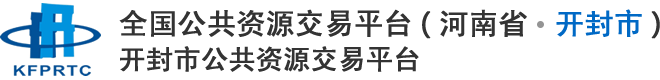清朝逼清为腐的“陋规”
发布时间:2025-03-19 14:54:49
浏览量:
发稿人:新澳门原材料1688大全
游宇明
皇权下的官员很容易产生腐败冲动,他们的官帽是皇帝赐予的,而非百姓施给,自然不必在乎百姓的感受。但公道地说,封建时代官员的腐败有些固然是因为个人的贪婪,有些也是被当时不合理的体制逼出来的。
众所周知,清代官场有所谓“陋规”,就是下级官员每年都得给上司赠送礼金。“陋规”名目繁多,比如漕规、盐规、税规、驿站规、平头银、冰敬、炭敬、别敬以及“三节两寿”(三节:端午、中秋、过年;两寿:上级官员及其夫人的生日)礼;数量惊人,一个巡抚、总督一年收入几十万两白银,不费吹灰之力。以前我一直认为所谓“陋规”完全等同于现在的贿赂,全部进了官员个人口袋。读了张宏杰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(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2月版)一书才明白:清代官员收受的“陋规”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用于公事,清官与贪官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收不收“陋规”,而在于他们是否将“陋规”全部用于公事。正因为“陋规”是地方公用开支来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,清代著名清官林则徐、曾国藩都曾心安理得地收过这种“陋规”。
这里不能不讲到清代奇怪的人事、财政制度。当时的总督、巡抚衙门都有一套行政班子,由幕友、书吏、仆役家丁们组成,负责办公、顾问、保卫、勤杂等事务。这些人所产生的开支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负责,但清政府规定:国家只给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开工资,需要人帮忙,得地方官员自己去请,谁请谁出钱。清代的地方官员也没有职务消费。请客、住房、坐车、出差、给上级领导买个纪念品什么的,都得官员个人掏腰包。工资不敷起码的支出,收受下级官员赠送的“陋规”。用于弥补公用经费的缺口,也就成了官场普遍的选择。
“陋规”是一种没有也不可能摆到阳光下的收入,以此中饱私囊特别容易。政府财政拨款规矩一般都相对严格,用于什么、怎样去用,用了之后如何报销都有定制,官员所得“陋规”如何使用,完全可以一个人说了算,用其办公当然没问题,将它装进自己裤袋一样没问题。事实上,专制时代官员借陋规大谋其私的现象如野草一样普遍,所谓。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就是这种现象的生动概括。清代公务员的工资是非常低的,曾国藩当了许多年两江总督,官当到了顶,也没有攒下多少钱来,一个比总督低N品的知府薪金能有多高?怎么可能攒下那么多钱?唯一的解释是清代官员个人致富靠的不是工资,而是腐败收入,具体地说是陋规。
对于“陋规”,清政府也不是不知道,然而,它更知道因为其先天不足的愚蠢体制,中央政府可以反腐败,但不能反得太厉害,否则,整个国家的各级地方政权立即会因无钱无人办公大崩盘。康熙皇帝曾说过:“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,即如州县一分火耗,亦法所不应取。”不过康熙接着还有下面“善解人意”的话:“若尽以此法一概绳人,则人皆获罪,无所措手足矣。”康熙48年9月,皇帝在给河南巡抚鹿祐的上谕中说:“所谓廉吏者,亦非一文不取之渭。若纤毫无所资给,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,何以为生?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,此外不取,便称好官,若一概纠摘,则属吏不胜参矣。”康熙的意思非常明白:你搞腐败是可以的,但要把握一个度,不能弄得鸡飞狗跳,毕竟,腐败得太过分,惹得宫逼民反,也不是一件好事。
然而,官员在腐败问题上一旦开了头就很难收手,纵观有清一代,固然有林则徐、曾国藩这样的清官,但和坤这种贪官似乎更多。对于官员,腐败本来就是一个无师自通的活儿,现在还有一个逼清为腐的制度,你叫他如何舍得放弃眼前这一块块的大肥肉?在如此体制下,官员腐败是必然的、普遍的、没有多少个人风险的,不腐败是偶然的、个别的、充满生命的血泪。
来自:《清风》杂志
- 上一篇:赵匡胤:以腐败换兵权
- 下一篇:陈云:三次拒修房 不吃“高级菜”
版权所有:新澳门原材料1688大全承办:新澳门原材料1688大全
地址:开封市市民之家五楼 邮编:475000 邮箱:[email protected] 网站备案号:豫ICP备12001764号-1
技术支持:郑州信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